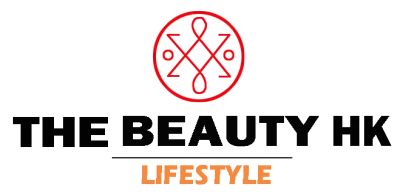-

冠狀病毒能否使遠程醫療墮胎成為新常態
2020-07-30 18:25:15 -

职场妈妈提前奶瓶训练失败,是婴儿抗拒奶瓶吗?
2022-01-21 12:20:25 -

我在阿薩姆邦旅行
2022-01-21 12:19:32 -

怎樣做才能存錢?才能錢滾錢?一起來揭秘!
2022-01-21 12:19:01 -

減肥期間可以吃的水果大榜單 看看你喜歡的在不在
2022-01-21 12:17:24 -

健康減肥離不開水果蔬菜蛋白質 注重比例就能瘦
2022-01-21 12:16:42 -

開始長斑了怎麼辦?這些去斑食物可以幫助我們抑制黑色素
2022-01-21 12:15:37 -

八個韓國明星韓國美白肌膚的秘訣
2022-01-21 12:14:39
熱門話題
我一直在我COVID相關媒體輪換小:紐約時報,一個地方新聞來源,並保持與艾米麗&Kumail,關於檢疫播客託管已婚創意團隊埃米莉·V·戈登和庫馬爾·楠吉尼。在第五集“ 2Fast2Serious”中,戈登和南吉尼讀了一位聽眾的信,描述了他們在COVID-19時期的“悲痛”。戈登讀完這封信後說,當今世界正在經歷的悲傷與父母在發現自己的孩子很酷時經歷的悲傷相似。“當您的孩子的情況與您想像的不同時,我認為這對父母有時孩子出來的父母來說是正確的,這是一段悲傷的日子,不是因為您不想讓這個孩子成為他們的真實身份,而是因為您有她在腦海中描繪出其他東西。”她說。
正如戈登所說,我是七年前在一個民間音樂節上見到我父親的,當時在一對啤酒的影響下,我告訴他我不是異性。他說他“明白了”,而我“正在經歷一個階段”。直到兩年後我打電話回家說我要和我的第一個女友約會,我們才再談這個話題。然後似乎打了他-也許這畢竟不是大學實驗。
當我到媽媽身邊告訴她時,她已經知道了,可能是由於我父親的幫助,並且打斷了我提出的所有與她必須做的事情交談的請求。她躲進了洗衣房,以逃避我們的談話很多次,我以為屋子裡的每件衣服都會分解。 我花了一年時間告訴她。當我終於對她說話時,她說的話-她愛我,但我可以繼續穿Portia de Rossi之類的衣服-並不是很難的部分,儘管她對社會期望女性女人穿衣服的方式有了教科書。
我是幸運者之一。在我告訴我的父母我被確定為酷兒之後,他們繼續告訴我他們愛我,幫助我支付房租,並保留我的食物,直到我完成大學。我再也不必擔心由於出來而導致的財務不安全感。但是有一個我從未理解過的調整期。為什麼他們花了幾年時間才與我成為誰?為什麼這種精神體操要接受他們的女兒不會嫁給高中男友的事實?我還是我; 我只是分享一些有關自己的信息。為什麼在我媽媽承認自己一直沒有女son這一事實之前三年過去了?當我回到家與第一任女友分手-我的初戀-為什麼我從家人那裡感覺到我不被允許難過嗎?
“對他們來說,一生的情節轉折對我來說並不奇怪。”
我為此一直生氣。當然,我已經像黏土一樣在療法中完成了工作。我已經前進了。我已經向我的父母介紹了我要嫁給的人,他們愛的人,以及我的父親與我的好朋友在他最喜歡的家鄉酒吧相伴的人。但是直到現在,我一直無法同情他們。當戈登將COVID的悲痛與父母了解孩子的酷兒的悲痛進行比較時,我意識到我最近的習慣與我出來時父母的習慣沒有什麼不同。我列出並管理我可以控制的東西。三月,我發明了我想听的故事-整個故事肯定會持續兩個月,我的未婚夫肯定會找回工作-並試圖忽略其餘的故事。談論這個話題使我感到緊張,就像我的性話題讓我的父母感到不舒服一樣。
對於這種疫情,我仍然不知道該如何應對。我現在知道它不會很快結束。我知道未婚夫不會在不久的將來恢復工作,我們計劃的任何重大旅行都將取消。我知道從自由職業者那裡休假一天就意味著沒收我在經濟衰退期間需要儲蓄的錢。而且我知道,就我的心理健康而言,我不舒服。但是我不想考慮任何一個。我不想接受明年我的婚禮可能看起來並不像我一直想像的那樣-我的大家庭成員中的每個人都在場。我不想改變我對未來的看法。
我和我的父母在幾件事上有分歧-目前,在政治觀點和CDC指導方針上-但是,儘管這種流行病具有所有負面特徵,但它啟發了我們的關係。我現在明白,當他們曾經喜歡公主和芭比娃娃的女兒告訴他們,確實,她喜歡公主和芭比娃娃時,他們感到震驚。他們從來都不願意把我所有的洋娃娃放在同一張床上主持的過夜活動,而肯卻在夢之屋的游泳池裡閒逛了幾天。對他們來說,令他們驚訝的是一生的情節轉折。
在我寫這篇文章時,我剛從家常便飯回家,面具緊緊地貼在臉上。我遇到了一群朋友,我們站在人行道上,緊張地閒聊著什麼。當我回到家時,我從其中一個人那裡得到了一條短信:“剛才看見你讓我的大腦短路了,”她寫道,“我不知道該怎麼做人了。” 我們誰都不知道我們在做什麼。這本不應該發生的。這是不正常的,儘管政府官員和衛生專業人員每天都告訴我們這是“新常態”。結果,我們當中許多人現在感到的是悲傷。Nanjiani告訴戈登:“對丟失的東西感到悲傷是可以的,即使知道丟失的原因是正確的。” 那是我七年前對父母的心態的理解所引起的。
我的父母沒想到有個同性戀孩子。他們沒想到我會告訴他們新的常態。我現在知道了 我也知道,在這種疫情期間,我對待自己的方式(要有耐心和耐心)就是我希望那時能對待他們的方式。七年後,我知道在不考慮其他現實的前提下過上舒適的生活意味著什麼。重寫規則很可怕。學習新事物令人恐懼。爸爸媽媽,很抱歉沒有看到那個。
現在,請戴上口罩,以便明年我可以沿著過道走。
我出來的時候我父母很傷心。最後,我明白了為什麼
- Colorfully
- Jul 30,2020
- 441 view

在疫情期間我第一次哭泣,當時我坐在我未來的姻親在曼哈頓公寓的白色沙發上。我和我的未婚夫正在看電影,講述那個意識到甲殼蟲樂隊從來沒有發生過的傢伙,所以他假裝自己是寫歌的人。這是一個偉大的概念,但一部糟糕的電影,儘管那不是促使我流淚的原因。我認為沒有人特別想到讓我抽泣,變成了恐慌發作。我記得我曾想過如果我在沙發上放睫毛膏,清潔服務可能會佔用我們婚禮儲蓄中的很大一部分。在世界衛生組織宣布冠狀病毒疫情之後的第二天晚上,儘管這並沒有引起震驚,但消息的結果是我,在這個昂貴的沙發上,試圖通過我的抽泣呼吸。
在確保沙發在驚恐症發作後保持不銹鋼狀態之後,我的生活開始著重於任務。我幫助未婚夫做些小手術的準備工作,這家公司叫出租汽車公司,這樣我們就可以在他們足夠好以直立時離開城市,然後開車帶我們回到新英格蘭。我買了兩個星期的食品雜貨,然後集中精力放在清單上,勾勒出隔離檢疫中新生活所需要的東西。我避免每天進行更新,除非我不得不寫關於它們的信息,並且當我知道我的朋友們想談論COVID時,我開始放棄Zoom呼叫。我用“淡淡的”浪漫喜劇控制了當晚的電影選擇,並撰寫了有關Netflix現實約會節目的作業,因此我不得不看著那些沒頭腦的東西“上班”。

我一直在我COVID相關媒體輪換小:紐約時報,一個地方新聞來源,並保持與艾米麗&Kumail,關於檢疫播客託管已婚創意團隊埃米莉·V·戈登和庫馬爾·楠吉尼。在第五集“ 2Fast2Serious”中,戈登和南吉尼讀了一位聽眾的信,描述了他們在COVID-19時期的“悲痛”。戈登讀完這封信後說,當今世界正在經歷的悲傷與父母在發現自己的孩子很酷時經歷的悲傷相似。“當您的孩子的情況與您想像的不同時,我認為這對父母有時孩子出來的父母來說是正確的,這是一段悲傷的日子,不是因為您不想讓這個孩子成為他們的真實身份,而是因為您有她在腦海中描繪出其他東西。”她說。
正如戈登所說,我是七年前在一個民間音樂節上見到我父親的,當時在一對啤酒的影響下,我告訴他我不是異性。他說他“明白了”,而我“正在經歷一個階段”。直到兩年後我打電話回家說我要和我的第一個女友約會,我們才再談這個話題。然後似乎打了他-也許這畢竟不是大學實驗。
當我到媽媽身邊告訴她時,她已經知道了,可能是由於我父親的幫助,並且打斷了我提出的所有與她必須做的事情交談的請求。她躲進了洗衣房,以逃避我們的談話很多次,我以為屋子裡的每件衣服都會分解。 我花了一年時間告訴她。當我終於對她說話時,她說的話-她愛我,但我可以繼續穿Portia de Rossi之類的衣服-並不是很難的部分,儘管她對社會期望女性女人穿衣服的方式有了教科書。
我是幸運者之一。在我告訴我的父母我被確定為酷兒之後,他們繼續告訴我他們愛我,幫助我支付房租,並保留我的食物,直到我完成大學。我再也不必擔心由於出來而導致的財務不安全感。但是有一個我從未理解過的調整期。為什麼他們花了幾年時間才與我成為誰?為什麼這種精神體操要接受他們的女兒不會嫁給高中男友的事實?我還是我; 我只是分享一些有關自己的信息。為什麼在我媽媽承認自己一直沒有女son這一事實之前三年過去了?當我回到家與第一任女友分手-我的初戀-為什麼我從家人那裡感覺到我不被允許難過嗎?
“對他們來說,一生的情節轉折對我來說並不奇怪。”
我為此一直生氣。當然,我已經像黏土一樣在療法中完成了工作。我已經前進了。我已經向我的父母介紹了我要嫁給的人,他們愛的人,以及我的父親與我的好朋友在他最喜歡的家鄉酒吧相伴的人。但是直到現在,我一直無法同情他們。當戈登將COVID的悲痛與父母了解孩子的酷兒的悲痛進行比較時,我意識到我最近的習慣與我出來時父母的習慣沒有什麼不同。我列出並管理我可以控制的東西。三月,我發明了我想听的故事-整個故事肯定會持續兩個月,我的未婚夫肯定會找回工作-並試圖忽略其餘的故事。談論這個話題使我感到緊張,就像我的性話題讓我的父母感到不舒服一樣。
對於這種疫情,我仍然不知道該如何應對。我現在知道它不會很快結束。我知道未婚夫不會在不久的將來恢復工作,我們計劃的任何重大旅行都將取消。我知道從自由職業者那裡休假一天就意味著沒收我在經濟衰退期間需要儲蓄的錢。而且我知道,就我的心理健康而言,我不舒服。但是我不想考慮任何一個。我不想接受明年我的婚禮可能看起來並不像我一直想像的那樣-我的大家庭成員中的每個人都在場。我不想改變我對未來的看法。
我和我的父母在幾件事上有分歧-目前,在政治觀點和CDC指導方針上-但是,儘管這種流行病具有所有負面特徵,但它啟發了我們的關係。我現在明白,當他們曾經喜歡公主和芭比娃娃的女兒告訴他們,確實,她喜歡公主和芭比娃娃時,他們感到震驚。他們從來都不願意把我所有的洋娃娃放在同一張床上主持的過夜活動,而肯卻在夢之屋的游泳池裡閒逛了幾天。對他們來說,令他們驚訝的是一生的情節轉折。
在我寫這篇文章時,我剛從家常便飯回家,面具緊緊地貼在臉上。我遇到了一群朋友,我們站在人行道上,緊張地閒聊著什麼。當我回到家時,我從其中一個人那裡得到了一條短信:“剛才看見你讓我的大腦短路了,”她寫道,“我不知道該怎麼做人了。” 我們誰都不知道我們在做什麼。這本不應該發生的。這是不正常的,儘管政府官員和衛生專業人員每天都告訴我們這是“新常態”。結果,我們當中許多人現在感到的是悲傷。Nanjiani告訴戈登:“對丟失的東西感到悲傷是可以的,即使知道丟失的原因是正確的。” 那是我七年前對父母的心態的理解所引起的。
我的父母沒想到有個同性戀孩子。他們沒想到我會告訴他們新的常態。我現在知道了 我也知道,在這種疫情期間,我對待自己的方式(要有耐心和耐心)就是我希望那時能對待他們的方式。七年後,我知道在不考慮其他現實的前提下過上舒適的生活意味著什麼。重寫規則很可怕。學習新事物令人恐懼。爸爸媽媽,很抱歉沒有看到那個。
現在,請戴上口罩,以便明年我可以沿著過道走。
推薦文章